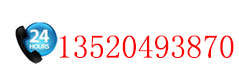截至2012年底,全球核電機組已累計安全運行了約13000堆年。但是,核電發(fā)展史中的核事故卻給核電發(fā)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,包括美國“三里島事件”及前蘇聯(lián)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”,以及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。核事故造成的經(jīng)濟損失,以及對社會和環(huán)境產(chǎn)生的影響是巨大的,日本福島核事故雖然沒有直接的健康影響可被識別,但在心理和社會福祉方面的影響,如抑郁癥和創(chuàng)傷后應(yīng)激反應(yīng),已在日本人群中觀察到了。事實上,在切爾諾貝利事故后,也觀察到了心理影響可能大于直接的放射性后果。核電廠核事故引發(fā)了人類社會的恐懼感,很多人對核電的發(fā)展有了不同看法。這種對核電事故所致危險看法上的差異,是由于各種社會因素引起的,主要包括:一是混淆核武器爆炸和核事故的界限,錯誤地把核事故與核武器爆炸聯(lián)系在一起;二是過分渲染核事故的影響;三是核產(chǎn)業(yè)長期封閉性造成的影響;四是若干核安全與輻射防護理念在理解和應(yīng)用中的偏差。其中前兩個因素屬于核事故引起社會響應(yīng)的外部因素,后兩個因素則屬于內(nèi)部因素。
公眾對核電發(fā)展的認知程度是內(nèi)陸核電建設(shè)的基礎(chǔ)保證。從“技術(shù)”上看,危險是一個用于表述與實際照射或潛在照射有關(guān)的危害、傷害后果的多屬性量,通常用可能產(chǎn)生特定有害后果的概率以及此類后果的程度和特性表述;它是衡量傷害和其概率的普遍的、基本的尺度。在這里所說的危險,實際上是危險的可接受性,而不是危險。危險是客觀的,危險的可接受性則包括許多社會的和主觀的因素。
解決核事故(事件)心理社會影響的基礎(chǔ)和前提就是預(yù)防與緩解并重。當(dāng)公眾切身感受到核能是安全的,核能可以造福人類,在給人類帶來極大好處的同時伴隨的風(fēng)險很小時,公眾對核的信任度將自然而然地會提升,恐核心理自然而然地會減輕,對核能的風(fēng)險承受能力將增強,從而有助于預(yù)防、減輕和解決核事故(事件)的心理社會影響。可見,提高核設(shè)施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。核事故(事件)社會響應(yīng)主要涉及核電廠營運單位、政府、傳媒、公眾等各個層面對社會響應(yīng)所承擔(dān)的責(zé)任,提出事故發(fā)生前、發(fā)生之中和發(fā)生后應(yīng)采取的解決核事故(事件)社會響應(yīng)的對策。這些對策主要包括:一是提高核設(shè)施與核活動的安全性,提高公眾對核的信任度;二是制定核事故(事件)分級的國家標準;三是建立事故(事件)發(fā)生之前的信息管理機制;四是建立事故(事件)發(fā)生之中的信息發(fā)布機制;五是事故(事件)善后處理期的社會傳播機制;六是建立公眾的信息溝通機制。
公眾是核事故(事件)社會響應(yīng)的主體,公眾對核事故(事件)及其后果以及如何防護自己等相關(guān)知識的了解、認知程度直接關(guān)系到心理社會影響的大小。除了應(yīng)加強核與輻射相關(guān)知識的宣傳、普及,最重要的是尊重公眾的知情權(quán)、參與權(quán)。為此,核能界必須在政府的領(lǐng)導(dǎo)和支持下,與科技、教育、傳媒等相關(guān)部門密切配合,建立與公眾溝通的有效渠道和正常的溝通機制。特別是環(huán)境信息知情權(quán)、環(huán)境信息傳播權(quán)、環(huán)境決策參與權(quán)和環(huán)境政策監(jiān)督權(quán)。